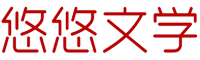笨笨/二姐
好久没有见着二姐了。
二姐坐在我身边,一会儿摸摸我的头,仔细分开一绺绺头发,说头发又少了,还有几根白发;一会儿拉着我的手,摸了又摸,说手挺白的,但还是那么小;一会摸摸肩膀,说越来越瘦……
我的心咚咚直跳,二姐会不会又把我抱在怀中吧!
家里人太多了,我都四十多岁的人了,当着老娘和妻子的面,二姐还是那么溺爱我,就像是自己的孩子。
这是我熟悉的,小时候老这样,被二姐摁在腿上,把头发一绺一绺分开,捉虱子,然后就是洗头,最后是洗手和洗脚。这是我最怕的,怕被二姐控制得死死的,不得动弹。
逃跑是没用的,二姐力气好大。
在野地里乱跑,从不洗手、洗脚、梳头,更不用说是刷牙了,只有二姐为我做这样的事。
梳头好像很疼,用石头搓手、搓脚也很疼,我不愿意,不愿意,一百个不愿意。二姐的那把梳子,还有搓手的石头,我很忌恨,曾偷偷地撂到地窖里。
上高中去住校了,二姐特意把她的一把塑料梳子塞到我书包里,还有一把牙刷、半支牙膏和一个搪瓷缸子。二姐说做高中生就要每天自己梳头,要刷牙,不能像个农民。
我是二姐的孩子。
二姐长我七岁。
那个年代,母亲忙着在地里挣工分,家里大孩子带小孩子。农村都这样。
据说,我小时候很胖,瘦弱的二姐抱着我很吃力,以致有一次不小心把我掉到土埂底下,差点没命了。父母屡屡提及此事。我不怪二姐,谁让我太胖!
我还能清楚地记得趴在二姐的背上,摆弄二姐两小辫子的情形,还有喂我饭的那个有豁儿的粗瓷大碗,和毛主席纪念章砸成的小勺子。因为有二姐给我喂饭,大人们说我快到四岁还不肯自己端碗吃饭。
二姐不识字,但她心灵手巧。针线活是一流的。除了带弟弟妹妹,全家的衣帽鞋袜基本由二姐置办。
二姐总能把哥哥姐姐穿过的衣服改得合身得体,让我们继续穿。边边角角的小布头会被缝制成小书包,我背着在小朋友中很有派头。
记忆中的姐姐,总是在油灯下搓麻绳,纳鞋底,做布鞋,织毛衣,永远没有闲的时候。
我是穿着二姐缝制的衣服和布鞋,走出山沟,又走遍东西南北。
除了纺线织布,母亲把自己的手艺全部传给了二姐,这令母亲很满意。她认为这是女孩子安身立命的基本条件,其他的对女孩子无甚用处。
然而,世事变化,不识字害苦了二姐,曾经引以为豪的手艺则变得几无用处。
记忆中的二姐,是那么的敏捷、有力。在河滩,总能捉住泥鳅一样的我,拎起来,任我脚踢拳打,奋力反抗,也能把我摁到河里洗澡。
二姐身体结实,是好劳力。种地、割麦、打场、挑担子、使牲口,样样能干,好多男人不能所及,村里口碑极好。
她是黄土地里的女中豪杰。
从第一次把束好的一担麦子放在我的肩上起,二姐就悉心教我干地里的活。我觉得她比父亲更能干,更有力气。她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很多,不光是力气。她教我,如慈母严父。
也有和二姐吵架的时候。
有一段时间,二姐放羊。每逢周末、假期,母亲就让我接替二姐,给二姐安排另外的活计。我讨厌放羊,也明明知道那是母亲安排,但常常把这怨气撒在了二姐的身上。结果,常常是二姐忍气吞声,从未向母亲揭发我。她怕母亲打我,她知道母亲下手是很重的。就算是我挨打的时候,也常常是二姐护着我。有时,我赌气不吃饭就去上学,常常是二姐拿块馍馍,追上我塞进书包。
我是那么一个拧巴的人。
上了大学,有一次也是负气出走。可走出家门后,身无分文,我不知道如何到省城,哪里去凑学费,哪怕只有区区百十来元,是二姐追了好几里山路,把两百块钱塞到我的手中。
青春年少的我,曾发誓不再让二姐遭受劳累,遭人欺负。哪知少年不经世事,生活没能如我意气行事。
二姐执意在黄土里耕耘一辈子,遁着最传统的伦理执着地坚守,在那个庞大的家族默默地奉献。个中委屈难于言表,苦与累就更不用说了。
可二姐包容了一切。
没人教二姐“海纳百川”,没人灌输她“锲而不舍”,也没有告诫她“天道酬勤”……而她朴素的意识里匡纳了所有经典和名言,她身体力行并自觉践行着我们不厌其烦推崇的人生哲理和伦理,是那么朴素、自然。了解二姐的人,没人不敬重。
二姐目不识丁,可她脑子里绝不是“丁”那么简单。
又见二姐,她依然像照顾孩子时的我一样,为我端水送茶,洗衣做饭,吃药加衣,嘘寒问暖,就连打洗脚水,洗袜子这些事,也争着亲为。也许,在二姐眼里,我还是那个需要照顾的孩子,而在我的心里,她永远是我融着浓浓母爱的二姐。
- 上一篇: 李茂林/塞北初冬
- 下一篇: 祝伟/老马(一个农民工的故事)
初次见面,请填写下信息吧:
相关文章
- 控制面板
- 最新留言
-
- 学校温馨小故事,创作不易,支持一个,谢谢。
- 故事记录了温馨幸福的生活,很感动,谢谢。
- 感谢网友的故事,用文字记录美好的人生。
- 五十年前,我在天水县一中读初中,王煜老师代过课,后来他当了副校长。昨晚突发奇想,在网上查询,一个是天水小学语文老师张健(小学名称名字忘了,只记得学校在北道阜),一个是天水县一中的马玉花,是我初中的班主任,好像刚结婚,一个就是王煜。张健老师身体不太好,不知道还在不在,马玉花老师现在应该有70岁了。
- 美丽的邂逅,在美还是故乡美!
- 感谢郭明祥老师,给于我们民族文化传承,弘扬的深情厚意的描绘!
- 现在还是小康就是四菜一汤
- 葫芦河公园的早上鸟语花香,风景宜人?
- 人间美味。
- 家乡的味道
- 文章归档
-
- 2024年10月 (153)
- 2024年8月 (18)
- 2024年7月 (5)
- 2024年6月 (35)
- 2024年4月 (4)
- 2024年2月 (16)
- 2024年1月 (62)
- 2023年12月 (715)
- 2023年11月 (595)
- 2023年10月 (382)
- 2023年3月 (12)
- 2023年2月 (135)
- 2022年12月 (155)
- 2022年11月 (429)
- 2022年10月 (8)
- 2022年9月 (30)
- 2022年8月 (121)
- 2022年7月 (358)
- 2022年6月 (99)
- 2022年5月 (589)
- 2022年4月 (141)
- 2022年3月 (322)
- 2022年1月 (9)
- 2021年12月 (8)
- 2021年11月 (92)
- 2021年10月 (35)
- 2021年9月 (58)
- 2021年8月 (3)
- 2021年7月 (4)
- 2021年5月 (7)
- 2021年4月 (86)
- 2021年3月 (99)
- 2021年2月 (69)
- 2021年1月 (145)
- 2020年12月 (72)
- 2020年11月 (53)
- 2020年10月 (5)
- 2020年8月 (8)
- 2020年7月 (12)
- 2020年6月 (116)
- 2020年5月 (15)
- 标签列表
- 友情链接